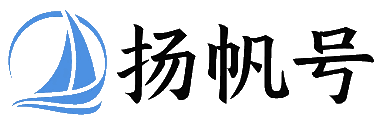1989年,画商黄江带领一批学徒从香港穿越深圳特区,来到紧邻布吉关外的大芬村。
这是一个以水稻种植为主要产业的自然村,人口只有约 300 人。黄江看中了这里的区位优势及低廉的房租和人力成本,借着正在开放的内地市场,选择在此继续从事西方古典油画的批量生产。这些绘画也被称为“行画”——黄江的学徒们按照图片手绘油画,作品达标后由黄江计件付费,之后批量销往海外欧美市场。
渐渐地,一些从内地来到沿海打工的年轻人也来到大芬,跟黄江学画画、做订单,一批上下游产业也聚集起来。“大芬村”自此走上了“大芬油画村”的道路。
大芬村以油画复制起家后,产业规模迅速扩大,在同类中脱颖而出,成为典型。在巅峰的 2005 年,欧美市场的油画复制品中有 70% 来自中国,其中 80% 来自大芬村。
这是大芬村发展的线索之一。

大芬村的另一条线索,是比这种商业、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稍晚出现的有关艺术和原创的叙事。
作为一个艺术品生产的场域,大芬村的发端却并非“艺术的”而是“商业的”,在其后续的发展过程中,始终无法摆脱受到的“抄袭”“复制”“缺乏艺术性”的批评。这些画复制画出身的画家们,也难以抗拒“原创”“创造”“文化”等概念的吸引。
这种复制与原创、商业与艺术的长期纠缠构成了大芬村与其他类似的艺术生产场域最显著的区别。从黄江落脚大芬至今的 30 余年中,这种纠缠几乎在每一位大芬画家身上都有所体现,也困扰过其中的绝大多数。
我在2019 年夏天第一次去到大芬村,那时候,村内的“墙面”画廊全部被拆除,各类违规搭建也一齐消失;2020年,受疫情影响,很多画家相继离开大芬村,曾经那种如火如荼从事油画复制品生产的景象已经成为过去时。在这种历史节点上,越来越多留在大芬的画家所思考的最重要问题也许是——“如何成为艺术家”。
一、“我只和‘原创’恋爱,不和‘原创’结婚”
2019年,我第一次见到虎子是在他的店里。
这是一家漂亮扎眼的画店,靠近大芬村中心,位于一个巷子的尽头,闹中取静。外墙被漆成海蓝色,挂着装饰品。店外的地上铺着木板,摆着休闲椅,围了一圈花草。一把阳伞常年撑着,供过路的人休息。

“我尽量保持店里很干净的,外面也是。”虎子坐在办公椅上,点起一支烟。他肤色黝黑,又高又瘦,看起来很干练。
在他旁边,展示着自己的作品,有海边写生,有江南水景,也有更具抽象风格、色彩运用更为大胆的乡村意象。
见到他之前,我听说他是一位“原创画家”。
2014年,是大芬村被国务院授予“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称号的第十年。深圳市龙岗区政府组织了一场“大芬十年”油画创作大赛,大约500名大芬画家在大芬美术馆前的广场上,露天现场作画竞技。虎子凭借一幅展现当时几百人现场作画壮观场景的作品,拿下了一等奖。
在此之前,他的生活遵循着大芬村最常见的路径。2006年来到大芬村,从学徒做起,随后尝试自己接单,开网店,租店面做画廊。那些年,虎子仗着自己年轻,常常画订单画到很晚,但这也意味着,他几乎一直没有自己的作品,全都是照着图片摹仿。

获奖刺激了虎子,他藏在心底的原创想法开始萌动。“那时候嘚瑟了几年。”
我指着周围的画问虎子:“这些都是原创吗?”“是吧。”他回答,但显得有些犹豫。
他用音乐打比方。”你听到一首新歌,觉得很创新,但慢慢听一下,再去找一下,会不会发现一些旋律似曾相识?你说‘创’了吗?”他笑着问我。“再荒凉的山上,都会有一两个脚印的。”虎子斩钉截铁地说,“所以没办法说清楚‘创不创’。”
几年前,虎子曾经创作了一幅画幅较大的装饰画,画面以稳重的灰色、暗红色为基调,配上一些图案。出乎他意料的是,这幅作品挂在店里没多久,就被一位散客买了去做家装。“我就发现这个构图其实很适合客厅装饰。”这之后,虎子连续创作了几幅构图类似、但又有所区别的作品,它们的市场反应都非常好。“你能分清它是不是原创吗?”
在和朋友的聊天中,虎子常常被人劝,有这么好的绘画技术,可以完全开始原创了,虎子不为所动:“你做得很超前,别人看得懂吗?”比赛获奖两年后,虎子的儿子出生了,店租、房租与日俱增。“我只和‘原创’恋爱,不和‘原创’结婚,”他决定现实一些,“你想要获得尊重,但你首先有没有尊重过你的家人孩子?让日子过好一点啊?”
二、“不要画坏了自己的手”
1985年,虎子出生在贵州。大概三四岁时,他像很多小孩一样学着画画玩。上小学时,美术课由语文老师教,有次虎子在课上画了一双运动鞋,“老师都没我画得好”。
身为苗族人,虎子十几岁时才开始学习汉语。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的各门文化课成绩都不好,最擅长的一个是体育,一个是画画,它们是虎子上学时自信的来源。那时候,虎子跳高、跳远、短跑,都能很轻松地拿到第一名,还接受过5年100米短跑的专业训练。
“但是后面又不自信了。”虎子说,“因为体育还是被人看不起,用体力,知道吧?(人们)比较看得起文化人。”就这样,虎子开始发展自己的另一项长项——绘画,在读中专时选择了设计专业,还在学校办过一次个展。
临近毕业,虎子又陷入迷茫。那是2006年,中专已经不再分配就业,这个学历在劳动市场上也非常不占优势。他也曾想过和很多人一样,毕业后到东部城市进厂打工,但一次暑假到东莞实习时在流水线上站了两个月,让他彻底打消了这个念头,“感觉挺憋屈的”。
决定去大芬村的契机很偶然。他在学校图书馆看到一份报纸,讲的是深圳一个土豪从美国买了十幅画,拿来大芬村装裱,装裱的人告诉他,这些画本身就是大芬村生产的。虎子意识到,在深圳有这样一个地方,可以纯粹依靠画画赚钱养家,决定去尝试一下。
临走前,虎子借老师的打印机印了一些国画和油画的图片,引起了老师的注意。这位老师一直很认可虎子的专业技能,还一度让虎子去他的公司帮忙,但看到这些印制的图片,往往色彩简单、构图平庸,“觉得有点‘行’”——也就是很标准化、简单化,很担心虎子“走歪路”,在临别前把虎子叫过去聊了很久。
“我老师是最早跟我说‘不要画坏了自己的手’的,”虎子回忆,“不能画那些花花绿绿的。”这个嘱咐虎子一直记到今天。

2006年,虎子刚来到大芬村时,只背了一个双肩背包,包里装着从网上打印下来的风景画和用剩的颜料。最初三个月,他一直没有找到稳定、理想的工作,直到在一个人才市场里加入了“老吴工作坊”——一个做装饰画的绘画作坊,才算入了行。
绘画作坊,这是大芬村最常见的生产模式,往往由一个老师傅负责接单和运营,雇佣年轻人作画,几个人各有所长,独立绘画。“你是画人物的,我是画抽象的,另外一个是做肌理的。”
虎子负责做肌理——在画面上人为制造一些笔触和凹凸的痕迹。一开始,工作坊的老板说虎子的水平可以直接出货,后来却一再推脱,说“还要再学三四个月”——“其实是利用一些年轻人(干活),又不付工资,”虎子告诉我,“是江湖骗子那种。”他做了一个月,直接离开了,”钱也没拿到“。
很快,虎子结识了一个老乡,对方正打算从画人物画转到装饰抽象画,两人一拍即合,开始做外贸订单。那是虎子的第一份稳定收入。一幅50*60厘米标准大小的作品,可以卖11-13块钱,一天可以画很多张。第一个月,虎子赚到了930多块钱,比当时深圳特区内外的最低工资高出了100-200元,而他的房租只需要大约150元。
在他们的工作室楼上,是一个专门画古典人物的工作室。一次,老板接到一些赵无极的抽象画订单,与自己工作室的题材相差过大,无法完成,就拿下来让虎子和他老乡各画一张样板,根据质量决定把订单交给谁。
虎子在上学时接触过国画和书法,画起赵无极带有东方韵味的油画时相对得心应手,很顺利地拿到了这批订单,与楼上的老板也建立了合作关系。不久之后,虎子搬出了原本的工作室,连续几年一直以赵无极的订单为主,慢慢成了大芬村画赵无极最有名的画家之一。
三、“伦勃朗知道吧?齐白石,他也是画订单的”
在大芬村,从画订单、画商品画变为自己创作的过程被称为“原创转型”,这往往充满复杂的取舍和现实的挑战,大芬村里的画家,几乎没有人能说自己完成了这样的转变。比赛获奖后,虎子也开始了自己并不顺畅的“原创转型”之路。
不久,虎子开始参加一个写生小组,每周定期聚在一起练习静物或人物写生。参与小组并没有严格的身份约束,所以成员在几年之间来来往往,但虎子一直没有退出。
比赛获奖两年后,2016年,虎子的儿子出生了,店租、房租与日俱增,“想得就更现实一点”。与很多人不同,虽然虎子已经在创作,但他并不对自己仍在接订单这件事遮遮掩掩,反而觉得很正常。“画行画也要自信一点嘛!”虎子说,“你去搞国展,我这些大芬画行画的跟你在一起展,一样获奖。”——儿子出生的同一年,虎子第一次入选一个国展,为申请中国美协的会员资格累积了第一个3分。
“伦勃朗知道吧,(还有)齐白石,他也是画订单的,《夜巡》他也是订单。说白了他就是帮一帮保安画肖像。齐白石画虾的,最早是木匠,他也画订单。徐悲鸿叫他去北京的时候,他也还混不开,也是要画订单。”
“人家不会为你的时间买单。”虎子把订单和创作划分得很清楚。他显然已经经历了太多类似的事情,面对那些自己认为很得意的作品,进店的顾客却可能只会当做“大芬的一幅画”。
“人来大芬想的是不一样的,他预设我花多少时间。他是跟你计较价格的,不会跟你说画得多好啥的。”在这些时候,“大芬”这个标签不再是行画生意中质量有保障的代言,反而成了画家们创作的阻力,个别画家在稍有名气后,还会刻意避开自己在大芬的生活经历。

一边接订单,一边搞创作、投展览,这种“两条腿走路”的策略看似简单,放在绘画这件事上并不容易。这不仅体现在两种画法的思维不同,而且在大芬村这个狭小的社会空间里,如果一个人声称自己“要搞原创”,会被认为不受控,各种合作机会就少了很多。
“就觉得(你是)画原创,不画订单的哦,谁也不找你。”虎子坦言,“我就‘明目张胆’地说,我是画‘商品’的,这样人家还带我做,是不是?”“说什么自己要搞原创?这留在心底就好了。”
四、“那不是我最好的作品”
2019年,是大芬村发展油画的第30年。这年夏天,当地政府开展了新一轮的环境整治,将大芬村内一度占据几乎每一面建筑外墙的“过道画廊”完全清除。曾经利用墙面作画、挂画的画家们要么进入楼房,要么离开大芬,昔日如火如荼的露天油画生产已不得见,如今的大芬村显得有些冷清。
虎子习惯在自己的画室里画画,这样能尽量避免被打扰,落得清净。他的画室一厅一卫,在大芬村旁的“画家公寓”(当地政府修建的人才保障住房)里,这是根据不同等级的美协会员来认证、分配的,能以极为低廉的租金为画家的工作生活提供一些保障。
推开画室的门,迎面而来的是浓烈的油料和丙烯味。画室里面积最大的一面墙是虎子工作的地方。为了提高效率,虎子与其他画家一样会把画布挂在墙上作画,既能站着工作、节省体力,又不必在乎颜料溢出画布——在墙上,印着无数个各色颜料组成的色框,那都是曾经挂在这里的画布留下的痕迹。

在那面墙的对面,不那么起眼的一侧,藏着虎子“原创”的一面。一些人物写生是虎子练习的习作,靠着墙的则是几幅画幅巨大的作品。它们纷纷背着我们,好像不想被人看到。“这是画了一半的,想要投展览,”虎子向我介绍,“但最近订单多,没时间画,投稿日期都快过了。”
2020年初,疫情爆发后,人们对艺术品、装饰品的需求瞬间降低,虎子的生意受到直接影响。那段时间,他把自己关在画室里,继续画些存货和创作。在大芬的十多年,虎子经历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2010年之后的国内市场兴起,还有持续不断的环境整治。
“我在大芬经历过太多乱七八糟的,这一次疫情不会打败我的。”虎子的心态非常好,“我来了14年,一直没有时间好好做过自己的事,有这么一个机会也不错,是不是?”
一年后,虎子的两幅作品接连出现在了两个展览中。
“你画完一幅画会签名吗?”我问虎子。虎子摇头:“人家不喜欢我签名,他有可能签自己的。”“你画原创也不签名吗?”我继续追问。“硬要的话,也有一些。”虎子沉默了一会儿,“说实话还是不自信,就感觉不是自己的作品。也有一些自己的艺术语言,但不是你最好的作品……我毕竟从小就画画。”
虎子的调色板总是最干净的,各种颜料严格按照色谱的顺序依次排开。虎子每次画完,一定要把调色板刮干净。他告诉我,只有这样,画出来才不会脏。